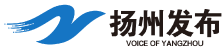通讯员 罗晨 梅浩 邵洁 郑洪雨 扬州发布记者 高宝亮 文/图
“我22岁嫁到宝女村,与大我5岁的孔庆如成婚。两年后,他在一起工伤事故中双目失明。为了这个家,我一边工作,一边照料着双目失明的丈夫,直到今年正月十一他去世。屈指算来,我照料他已经51年。”4月9日上午,在杨寿镇宝女村75岁的张正英的家中,老人眼角泛起泪花。
最伤感:飞溅的炽热金属碎片伤害的岂止是眼睛
春日和煦的阳光下,集镇一排店铺后面的民房显得有几分静寂。室内是两张简易的桌子和几张凳子。靠墙的方桌上放着两束花,中间是老伴孔庆如的遗像。张正英一边小心翼翼地用干布擦拭镜框,一边喃喃自语:“孩子他爸,你在那边还好吧。”
张正英,1949年出生。“我娘家在方集村,22岁那年,我结识了李岗村(宝女村的前身)青年孔庆如。相处一段时间后,我觉得他沉稳大气,拿现在的话说,人比较靠谱嘛。”张正英回忆,孔庆如当时在集镇农具厂工作,每月工资只有19元钱。为了把日子过得好一点,他就到安徽天长县一家小厂去揽活,加工锉刀,这样月收入就有40多元。婚后的第二年,张正英当上村里的妇女主任。
1973年初春,那天她去开会,突然有个村干部对她说,“你怎么还在这里坐着呀,你丈夫眼睛受伤了。”
匆匆跑到小厂一了解,原来是加工锉刀过程中,一块炽热的金属碎片飞溅而出,击中了眼球。“本来他有一只眼是好的,只有一只眼视力在退化。医生讲,碎片直接击伤了眼球,没法复明了。”

最难忘:那一次次跑医院的日子
当时她才24岁,前一年儿子刚刚出生。这一意外的变故,让一个本来充满希望的家庭一下子阴云密布。“这日子看不到希望了,不如离婚再嫁,你还有一次选择机会。”有人帮她出主意。
在农村,许多体力活要靠男人来顶,让一个女子撑起一个家,不是一般的难。
“24岁的年纪不算大,再嫁不难。可我这一走,才一岁多的儿子就成了没娘的孩子,孔庆如生活也不能自理。这个家就散掉了。”张正英表示,再难也要咬牙挺下去。
于是,那几年里,她带着丈夫跑遍扬州、仪征、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。一次次充满希望,一次次回归失望。面对一次次落在病历上的诊断,她仍旧不死心。“会不会随着年龄增大,受伤的眼球会逐步恢复视力?”面对她的发问,医生只能实情相告:“瞳孔受到这样重的伤害,基本上是不可逆的,可能要终生失明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人的视力只会逐步减退。你要有心理准备。”
从那以后,张正英开始了日复一日照料丈夫的日子。每天早上,她早早起来煮一家人的早饭。然后,帮他倒水,挤牙膏,照料他洗脸,整理房间的卫生。然后,再照顾他按时服药。家里没有自行车,她天天步行15分钟,到村里上班。
天气晴好的时候,她就骑三轮带着丈夫到湖边“观光”,到邻居家和村民聊天。镇里、村里有文艺演出,他就带丈夫去用心“听”扬剧、歌舞演出,现场感受那份热闹氛围,抚慰丈夫的情绪。

最温暖:生活像甘蔗,尝过了艰辛,越吃越甜
因为工作出色,1979年,张正英如愿入党,后来还被评为省“三八红旗手”。
丈夫身体康复到一定程度后,夫妻俩一起打草帘卖到砖瓦厂,赚一点手工钱。“他眼睛看不到,心里明白呢。把他带到架子前,他就在那里手不停脚不住地干。我就在他身边搓草绳。一干就到深夜一两点。那时候,一条草帘才卖九毛钱。可是这一季劳作,几乎解决了一家人温饱。”
有一次,镇领导带着机关干部下村支农劳动。劳动间隙,一位镇领导说,张正英家离这里近,我们到她家去喝口水。到她家后,发现一男子在家里默默地打草帘,就问身边人,这人谁呀?有人就悄悄讲,这是张正英丈夫,双目失明了,一家人生活困难。望着这个几乎没有一件像样家具的家,镇领导把张正英拉到一边:“你家这么困难,怎么没见过你打过申请救济的报告?”
张正英脸红了。她沉吟着说:“不是不想。可是村里比我家困难的不在少数。救济金就那么多。我是党员,我要跟村民争那碗水,村民会怎么评价村干部?怎么看村里的党员?再说,我还苦得动,能自己解决,不能让群众吃亏。”
镇村干部们都被这番话打动了。没有人说话,但人人心中有杆秤,称得出人的斤两。
三天后,砖瓦厂打来电话,让她把做好的草帘全部送过去。事后,她才知道,镇领导为她家积压的草帘专门打了电话。
“生活像甘蔗,尝过了艰辛,你才越吃越甜。”回首往事,张正英无限感慨,是党组织的关爱,是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之光,照进了这个多难之家。“在最困难的时候,我的一句孩子他爸,别怕!真的给他带来力量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