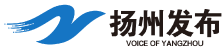■邱凤莲
她是一团火。有时明亮温暖,有时火热炽烈。有时在戏里,有时在戏外。
知道汪琴这个名字,是在很小的时候。那时候农村渐渐有了收音机、录音机,每日里,小小音箱传出的声音在小村庄的空中流转,织成了村居生活之外的新世界。
上世纪80年代,人们的生活没有现在富足,一台小小的录音机对于当年的很多农民来说已属奢侈品。但在那个万象更新的时代,人们虽缺钱,却不缺梦想和激情。你听,无论哪家打开录音机,左邻右舍便跟着哼哼唱唱起来,人们共享着那充耳盈面的艺术气息,也过起了简简单单的艺术生活。
那时候,汪琴是父辈们常提的名字,因为她是唱扬剧的名角之一。我虽然很小,也记住了这个名字。人们或从剧院里,或从那些磁带封面上也渐渐识得了她的样貌:俏丽的面容、传神的双目、灵活的身段。这印象多多少少也留在了我的心里。只是对于年幼的我,这印象有点模糊。
1988年,我考入师范,和汪琴、刘葆元夫妇的女儿晓畅成为同窗好友。从此便和两位扬剧艺术家结缘。
第一次见到他们夫妇,是在扬剧团旧楼他们家里。晓畅一进门,刘伯伯就用扬州话大声嚷着:“我的鞋子(扬州话“鞋子”与“孩子”同音),我的袜子。”我被他的幽默逗乐了。
一个16岁的乡下孩子,第一次踏进两位剧团前辈的家里,多少有些拘谨。不过,刘伯伯的健谈和幽默,很快让我放松下来。汪琴阿姨和刘伯伯不同,她温婉和气,初见时言语并不多。那一天,我感受到的是这团火焰的安静和温暖。及至后来,看她不惧艰辛到各地一场接一场地演出,再了解她扮演的那些颇具个性的人物形象,我渐渐从那些不仅有冰雪之志,更有火焰之烈的童玲、刘翠娥、顾二嫂们身上,感受到了汪阿姨这团火不仅是安静温暖的,也是深沉热烈、光芒万丈的。
汪阿姨家屋子不大,但家里的布置充斥着文艺气息。他们夫妇的话题几乎都是戏。我不了解那些角色,也听不太懂。我记住的只有刘伯伯绝佳的厨艺,他做的菜好看又好吃。我也明白了晓畅为什么诗书画艺、歌舞弹唱样样皆精,源头就在这个家里。
后来我工作了,去了瓜洲。暑假有时也会和晓畅约了一起玩。有一年,从黄山回来,我顺便给他们夫妇带去了当地的茶叶。他们硬是不肯收,说小朋友来玩就好,这茶叶留着回家孝敬我父母。偶尔带些水果去,他们也要回赠我其他东西。直到我长大些,才渐渐明白,他们其实是体谅我家在农村,工资微薄。
有一次汪阿姨去瓜洲演出,给我留了一张票。剧情已经记不清了,可是却清楚记得舞台上她饰演的人物形象。那是一出女性悲剧,舞台上的她,将深情、激情、悲情都融注在婉转的唱腔和精细的做功里,那声音,那舞姿,既有“间关莺语花底滑”的妩媚灵俏,也有“幽咽泉流冰下难”的凄恻无奈。一唱一念、一颦一笑、一行一止中,演绎的都是主人公的寸寸柔肠,铮铮心曲。我坐在台下,觉得无可名状,却又丝丝入扣。
那时候,剧场条件简陋,他们一连几天在这个江边小镇演出其实很辛苦。印象里,我还从家里带了几斤大米去给他们熬粥。但他们不言苦,那个小小的舞台点亮了小镇的夜晚。
江涛阵阵,一火独明。
是火焰,就要照亮,就要温暖。而她,还想保存火,传递火,给更多的人,给未来的人。所以,她和先生一起成立“汪琴艺术团”,一次次把戏送到乡村;所以,虽已是耄耋之年,她依然登台演出。
舞台无大小,每一场她都全力以赴,以火的热情照耀周遭。
上月,接到汪阿姨电话,闲聊间听闻她出了新书,我便兴致勃勃去取。
一见面,阿姨照例抱抱我,还是那样亲切温暖。在她面前,我好像又变回了小孩子。那个16岁的我,懵懵懂懂站在她门前,我们彼此打量的第一眼,我感受到的暖,隔着30多年的岁月,依然在我们彼此间荡漾。
阿姨告诉我,我的文章,她每期必读,并且都收藏着。我心里惭愧并感动着。老人家已经85岁高龄,依然身段轻盈,语音清亮,真是令人佩服。桌上是一本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汪琴谈艺录》。淡紫色的封面上,身着红色唐装的汪阿姨,依然是那样神采奕奕。我注意到封面上写着“汪琴著、刘葆元记录、刘炼策划”几个字,想象着老两口一个说一个写的琴瑟和鸣,不觉笑了。
老两口商量怎么给我签名的细节,最有趣。刘伯伯已经下笔,写着写着停下来说,“叫邱凤莲小朋友,也不小了,叫邱凤莲女士、同志,太生分了……”沉吟间,汪阿姨接下去:“就叫凤莲儿,这么多年了,可不就是我们的孩子一样。”
我心里又暖了一下。
汪阿姨和刘伯伯之前合著的一本书,叫《火之韵》。这题目,多适合她。我就借来一用吧。
作者简介:
扬州一阅全民阅读促进中心联合发起人,高级教师,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,国家教育科研优秀教师,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,江苏省扬州市特级教师。著有《大声读给孩子听》《好童书好课堂:整本书阅读与教学20例》《中国古代神话》等,主编《读写课》等。

《扬州晚报》版面